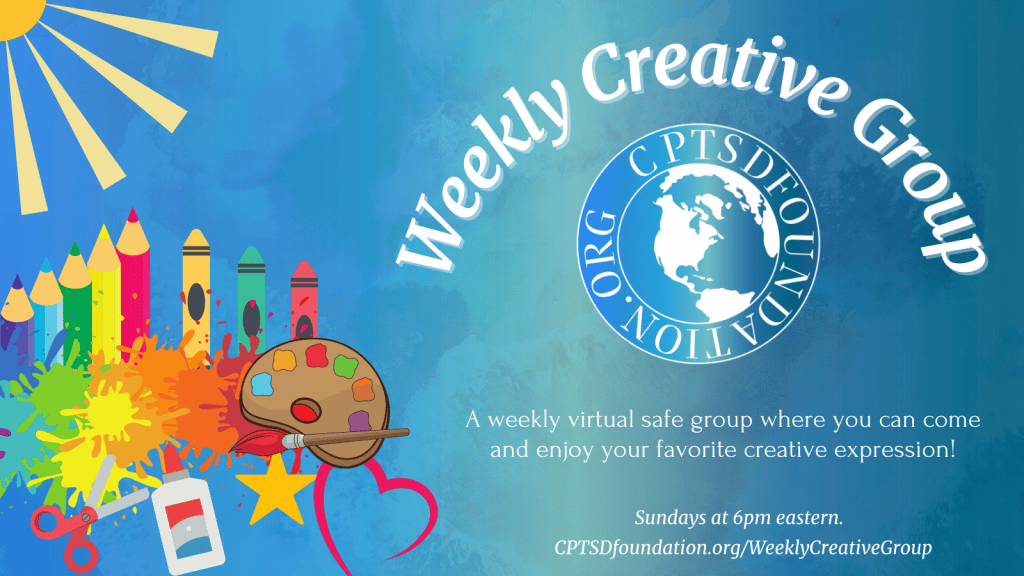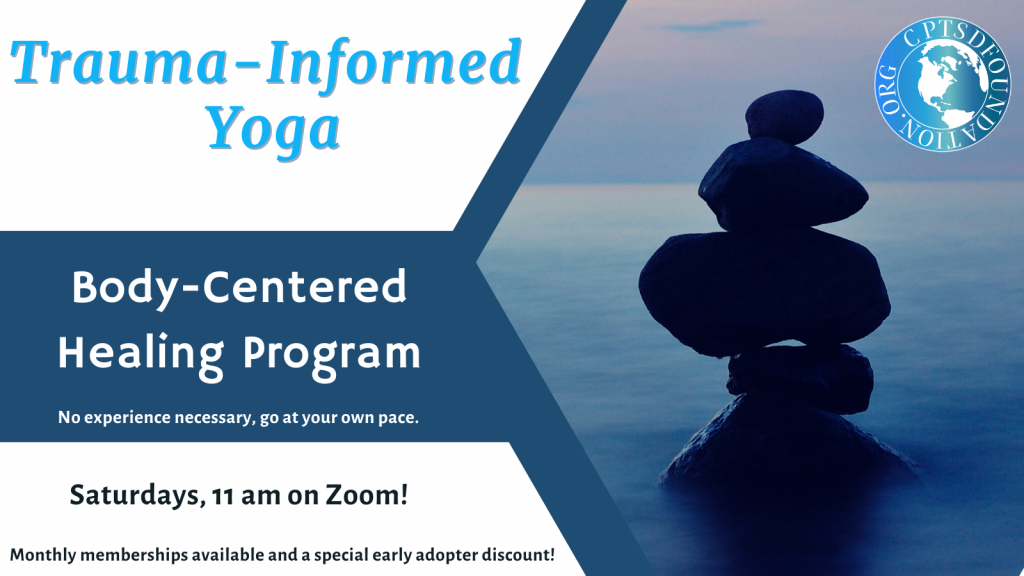孩子经常提出情感小丑甚至情感对象,但我的教养是一个被忽视的场景:被提出作为一个人类的毛绒玩具。
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是多么有害我的教养直到十九岁,被诊断为C-PTSD。一个月后,我被一个精神病区了五天。除了被隔离在一个环境被精神虐待,我真正的损害是侮辱和长篇大论的向我投掷通过童年。
然而,它是尝试此种疗法(眼动脱敏和后处理)疗法在二十岁,发现我面临near-hourly基础上的退化。上高中的时候,我母亲的填充动物玩具是我的社交生活的关键。他们是我的早晨,中午,晚上。他们为什么在课堂上我的手机拿走,不是Instagram。她是我每日的喉咙疼痛持续紧张我的喉咙给填充动物玩具尖锐的声音让她笑。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的笑容如此明亮的笑如此自夸地当我是一个洋娃娃。在这一点上,我已经习惯了悲伤从我的童年慢慢恢复正常,但从未像这样。
像许多其他的孩子一样,我被心仪的,迪斯尼,以及其他形式的拟人化媒体和参与。然而,我变得越老,人类我就越少。我的母亲,我几乎是伊丽莎白。除了她的“瑞”(简称“亲爱的”)经常被她与猪emoji,我是莎莉羔羊,乔治乌龟,诺曼·熊,数万人。她自己也有类似的身份和昵称。这种形式的沟通,用她的话说,她向我展示了她的爱,我们如何保持和平,“空调我生活在一个连续状态的回归。这些长毛绒裤住在汽车杯座,沙发,甚至在我们的餐桌上。花许多小时后成许多夜晚对我大喊大叫,她躺在我的床上,放纵我的喜欢米拉大象和Petie企鹅第二天早上。的鞭子的溺爱或者侮辱了真的是开创性的。我的身份是由她的情绪。
居住在这个虐待回答这么多问题。难怪我的心灵感觉太分散。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我是否考虑过自己的幸福。我日常的内心独白,“妈妈工作很努力。她有那么多会议。她总是堵车。“我自动提交每一个辗转反侧的夜晚让她笑,微笑,即使考虑到这意味着铸造我的生活。它超越痛苦的意识到,我的存在是一个多种形式的退化状态。对她来说,我的理想状态必须为她的毛绒动物玩具,低于低于人类的财产,为了让家庭正常运转。缺乏尊严之后我感到是如此猛烈,我差点自杀未遂。
我怎么能找到任何表面上的自我的碎片下面当我埋我是谁了?幸运的是,我有好朋友和亲密的大家庭。我开始更频繁地联系他们,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支持比我所能想象的。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与填充动物能够驾驭自己的关系成为了一个解放的经历。它不应该被解放,但我很高兴。不断羞辱的一线希望的童年是它真的集酒吧非常低。甚至是陌生人能实现的期望,没有见过在家里:自动尊重、平等的情感,和被视为一个人叫伊丽莎白。我不能容忍被当作什么少了。
帖子免责声明:任何和所有信息共享这个客人博客的目的是仅供教育和信息的目的。没有在这篇文章里,在CPTSDfoundation.org上也没有任何内容,补充或取代和方向的关系你的医学或心理健康提供者。的思想,想法,或作者所表达的观点这客人博客不一定反映CPTSD基金会。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我们的隐私政策和免责声明。

找到目的在视觉和情感上的灵敏度和强度通过艺术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