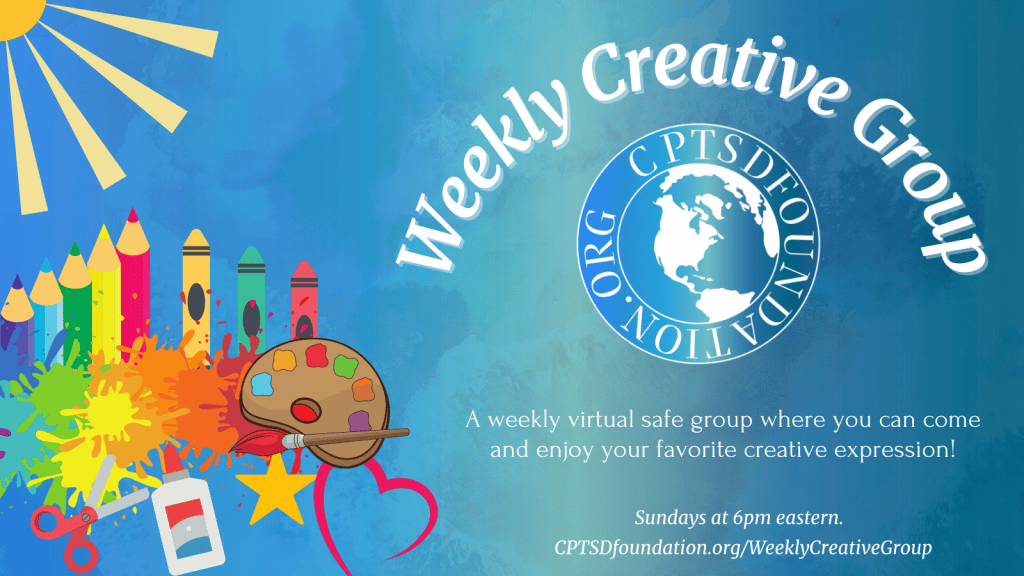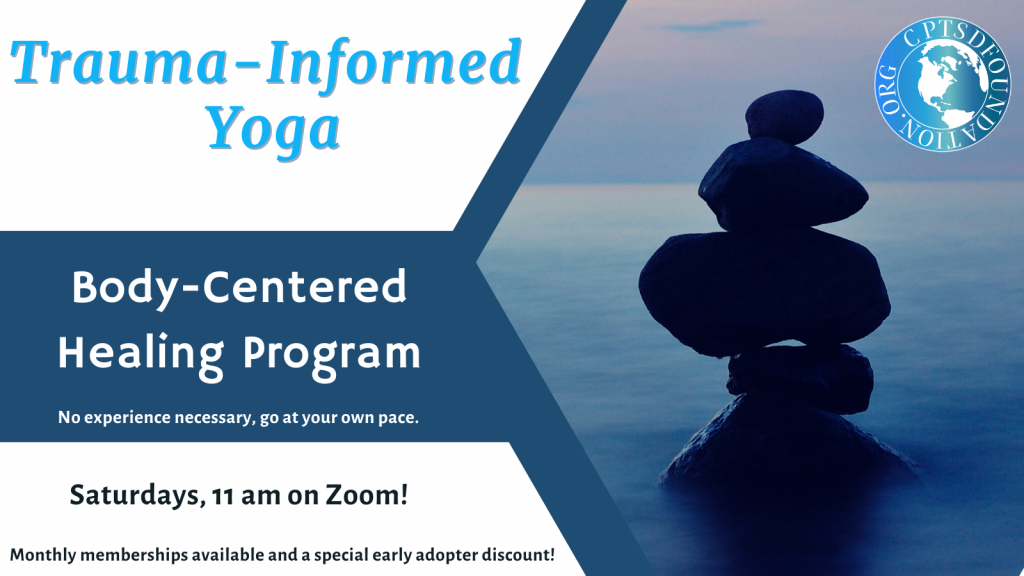怨恨就像喝毒药,等着对方死去。”
~匿名
当我向人们提起宽恕这个词时,大多数人都会叹息一声。这种情绪通常表现为“我已经尝试过了”、“祝你好运”或“真辛苦”。在我们的现代文化中,宽恕似乎是一座要爬的山,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在最坏的情况下,是一个无法到达的目的地。但在我的治愈之旅中,我发现了观点和坚持的转变。我们常常把诸如幸福、爱、价值和自尊之类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他者”或“独立者”,而现实是,通过我们愿意成为周围世界的学生,我们更接近我们想要的结果。当我们改变看待自己的方式,朝着我们想要在生活中创造的更大结果前进时,曾经不可能克服的障碍变成了改变我们的旅程。
“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目的地。”
——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
作为一名童年性虐待的幸存者,宽恕绝非易事。与施害者一起成长的困惑,以及一个没有保护我的家庭,给我留下了深深的信任创伤,这是一个由无意识的愤怒和不稳定的依恋组成的迷宫。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不相信自己身体和情感上的感受。然而,每一个改变和向前迈出一步的选择和决定,都为我创造了一种动力,让我开始对自己的经历和生活承担全部责任。从设定新的界限,日常的自我照顾,到尝试新的疗法和拥抱我自己的精神品牌。一点一点的增量转变允许意愿、开放或仅仅考虑宽恕的量子转变发生。
“要么做生活的学生,要么接受教育。”
那么我说承担全部责任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从“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变成“我能从中学到什么?”或者“这次经历教会了我什么?”我们开始从我们感到无助和受害的情况中重新控制我们的生活。
我并不是说这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也不是一夜之间的转变,但当我们开始转向赋予自己权力时,个人责任是第一要素。
- 全部责任不意思是你的虐待是你的错
- 全部责任做的意思是你要为自己如何处理它以及如何处理你的痛苦负责。
“一个常见但错误的想法是,宽恕意味着让伤害你的人摆脱困境。然而宽恕并不等同于正义,也不需要和解,(沃辛顿)。例如,曾经的虐待受害者不应该与仍然具有潜在危险的施虐者和解。但受害者仍然可以得到同情和理解。“无论我原谅或不原谅都不会影响正义是否得到伸张,”(沃辛顿)。“宽恕发生在我的皮肤里。”(堰,2017)
当我们掌握了自己的生活,并选择做出艰难经历要求我们做出的调整时,我们不仅赋予了自己重新掌控生活的能力,同时也释放了我们无法控制的东西,让我们的痛苦引导我们通过一个不仅能治愈我们,还能改变我们与世界互动方式的门户。
“上帝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事情;赐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事情;赐予我智慧,去分辨这两者的区别。”
~宁静的祈祷
这看起来像是有更多的能量,感觉更强的目标感和联系感,更少的压力,更平静的头脑,更放松的身体,更深入的情感,更高水平的幸福,更深刻的治愈经历。这些选择为我们的痛苦负责,放弃对责备和伤害的执着,是宽恕的基石,并为宽恕提供的更大的治疗模式转变创造动力。
我的宽恕之旅:
Bob Enright博士是国际宽恕研究所的联合创始人,他将宽恕分为四个阶段。
- 揭露阶段或(揭露自己的愤怒)
揭露阶段构成了意识的开始,情感的剧变和痛苦伴随着我们可能经历的任何创伤或不公正的完全理解和感受而来。(Enright, 2022)
“在你让无意识成为意识之前,它将指引你的生活,你将称之为命运。”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我已经跑了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感觉,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有那样的行为。从学习成绩差,精神健康问题,蜱虫,到故意破坏,过早饮酒,吸毒和盗窃。我很生气,虽然我没有意识到我的身体发生了什么,但我的潜意识为我做了这件事。我的痛苦无法抑制。高中毕业晚了,背着背包离开了我的家人,坐着货运火车穿越了美国,但痛苦仍然存在。没有足够的大麻、距离或分心可以把它赶走。我离我的家人越远,我就越感觉到它就像一个不舒服的胃在我身体深处汩汩作响。我穿越了整个国家回去看了一遍。那年冬天,我在加州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个农场里生活和工作,我从那里回到底特律,回忆起那次虐待。那是泪水和了解的洪流。 A voice spoke deep down from inside me, it wasn’t my own conscious voice but an echo from a little boy who had never been heard or seen. One evening in my parent’s house after my family had flown me back for a week at Christmas time, I told my brother and sister what had happened. Our father had molested me. Crying intensely the tears felt as though they had come from out of nowhere a sense of detachment from what I had spoken encompassed the whole experience as many more spontaneous fits of crying would follow throughout the week, still unable to feel the weight or emotional context of what was beginning to surface. It wasn’t till I arrived back at the farm that my friend Andrea looked at me and told me, “Jeff, I don’t think going back there was good for you.”
回到加州,我和哥哥姐姐分享的东西很快从我的脑海中消失了,因为我的情感开始回忆起我脑海中已经有的东西。不久,我在农场的季节性工作结束了,我发现自己情绪混乱。在面对不可避免的回归街头的前景时,无法感受到情绪的稳定。我在农场的朋友安德里亚同意和我一起去,因为他对乘坐货运列车很好奇,完全不知道我内心有多挣扎。当我们一起离开农场的时候,我成了一个精神压力山大的人。在街上生活的不稳定和压力,再加上创伤的巨大重量,让我没有出口或应对的方法,我唯一想做的就是逃跑。
对安德里亚大发雷霆,悄无声息地把他推开,我们的友谊开始破裂。在洛杉矶的海滩上,他的耐心已经耗尽了。告诉我他打算彻底离开。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一直被强烈的情绪所压倒,也没有意识到我对他的推拉行为与我对父亲的记忆有任何关系。当安德里亚站起来转身离开时,我内心的某种东西又一次爆发了。在泪水中,我找到了我不经意间对哥哥姐姐说过的熟悉的话。我感觉好像知道他是我唯一的安全或希望。他坐下来,一直等到我不哭,看着我,告诉我他会确保我得到帮助。
2.决定阶段(决定原谅)
当一个人意识到继续坚持任何创伤或不公正最终会带来更大的伤害时,决定阶段就发生了,选择原谅已经成为一种选择。(Enright, 2022)
“F-E-A-R
操死一切然后逃跑
或
面对一切,站起来”
我离开街头已经两年了。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定居下来后,我经历了一系列不稳定的住房状况,因自杀而住院治疗,现在终于有了工作,有了家,还有了家 治疗师。有一天,坐在她的办公室里,她告诉我,她年轻时也有过类似的虐待经历。我很惊讶,因为她看起来如此稳定和强壮,这给了我希望。她坐在椅子上看着我问道,你觉得有一天你会原谅我吗?我内心深处知道,这对我和我的经历都是很重要的,但我无法释怀,更不用说对我所经历的记忆和创伤放松了。“也许有一天,”我告诉她。
治疗师。有一天,坐在她的办公室里,她告诉我,她年轻时也有过类似的虐待经历。我很惊讶,因为她看起来如此稳定和强壮,这给了我希望。她坐在椅子上看着我问道,你觉得有一天你会原谅我吗?我内心深处知道,这对我和我的经历都是很重要的,但我无法释怀,更不用说对我所经历的记忆和创伤放松了。“也许有一天,”我告诉她。
3.工作阶段
这包括愿意观察和理解为什么伤害者会做出他们所做的事情,并开始培养同理心,不是原谅,而是人性化的犯罪者。这一阶段还包括接受痛苦,以便为不公正所带来的痛苦承担责任,而不是通过将痛苦转嫁给他人或回馈给犯罪者来避免痛苦。可以向违规者提供善意,同时根据个人认为安全与健康的情况,保持适当的安全和界限。(Enright, 2022)
随着我的成长,我的生活变得起起伏伏,充斥着日常生活的琐事,要协商账单、工作和朋友,但总是要处理我的创伤。这种痛苦不会消失,它一直在着色,并在我与世界的互动中表现出来。我对我的父亲和祖父非常愤怒。我会在治疗中尝试所有我能找到的方法。从呼吸测试和核心能量测试到甚至有一段时间我假装杀死了我父亲和凶手。发泄愤怒是一种治疗方法,但正如我的治疗师警告的那样,最好是发泄出来,继续生活,而不是坐在那里。通过网络脊柱分析等非常规疗法寻求更多帮助,我发现自己失去了长期积累的愤怒和怨恨。当我想到父亲时,我感到的痛苦的愤怒和情感上的不适慢慢地开始消散。我的身体开始感到更轻了,我没有那么紧张了,有了那种轻松的感觉,我可以放松到一个更中性的地方。我不是我的创伤,我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虽然我不想在现实世界中与父亲建立关系或和解,但我开始看到情况是什么以及他是谁。
4.成果/深化阶段
个体开始从创伤的痛苦和负担中看到缓解和进步。可能会在经历的痛苦中找到目标。可能会发现生活的新方向。理解宽恕的悖论:当我们给予他人并爱他人时,我们也会得到治愈。
(Enright, 2022)
“当你勇敢地面对发生在你身上的痛苦,并向伤害你的人提供善意时,你就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堰,2017)
慢慢地,我开始发现自己深入到痛苦的深处,也超越了痛苦。我变成了另一个人。的确,我无法挽回发生的事,但现在即使我可以,我也不会。我知道,现在的我比过去的我更好、更完整、更快乐。我很感激。很多时候,这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治愈和改变的过程。我看到了父亲的本来面目,一个受伤的人,他一直没有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承担责任。是的,我很生气。是的,这很痛苦,但现在我被赋予了力量,因为我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我选择直面我的痛苦,承认它,而不是把它传递下去。 No longer could he intimidate me and no longer did I need to hide what had happened. Instead, I chose to transform it. In 2021 I sold everything I owned and bought a one-way ticket to Italy. Since then I finished 写一本关于我的经历,关于我的创伤和流浪街头的经历的书。建立一个演讲项目,我开始与欧洲的年轻人分享我的故事。我分享的越多,我就越意识到我们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也越意识到这种创伤是羞耻和孤立的创伤。当我诉说痛苦时,我戴上的面具消融得更厉害,我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无法言说的隔阂也变薄了。在这一点上,我发现我们确实是彼此的反映,我的宽恕是一种选择,不再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控制我是谁。
写一本关于我的经历,关于我的创伤和流浪街头的经历的书。建立一个演讲项目,我开始与欧洲的年轻人分享我的故事。我分享的越多,我就越意识到我们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也越意识到这种创伤是羞耻和孤立的创伤。当我诉说痛苦时,我戴上的面具消融得更厉害,我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无法言说的隔阂也变薄了。在这一点上,我发现我们确实是彼此的反映,我的宽恕是一种选择,不再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控制我是谁。
我的愤怒是如此的红
热脉动
我把它浇在水里
看着它从我的心中通过我的眼睛流出
我呼吸
我们把愤怒当作盔甲随身携带,保护自己
与我们所属的世界抗争
对抗自己
我感觉它破碎了
我感到镜子的碎片掉到了地上
我再也看不到破碎的倒影
但我却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我是整个世界
~杰夫Spiteri
客人帖子免责声明:本博客中分享的所有信息仅用于教育和信息目的。本文中的任何内容,以及CPTSDfoundation.org上的任何内容,都不是对您的医疗或心理健康提供者的关系和指导的补充或取代。本博客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想法或观点不一定反映CPTSD基金会的观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我们的隐私政策和完整免责声明。
杰夫·斯皮特里(Jeff Spiteri)是一本未出版的回忆录《内心之桥》(the Bridge Within)的作者,这本回忆录记录了他作为一个无家可归的年轻人在美国各地乘坐货运列车的经历,以及他在途中发现的童年创伤。杰夫很自豪地用他的声音作为影响、指导和影响年轻人和教育工作者的工具,分享他的经验和工具,以恢复和治愈。